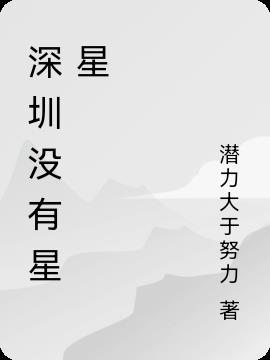第1章 消失的光
窗外的深圳像一块被过度曝光的电路板。深南大道车流拖曳出的猩红尾灯,平安金融中心刺破夜空的冰冷尖顶,还有远处腾讯大厦永不熄灭的蓝白色巨幕,将人造的光污染泼洒进福田区这间高档公寓的客厅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紧绷的静默,是中央空调恒温系统低沉的嗡鸣,是扫地机器人无休止的圆周运动,是林岚修剪得一丝不苟的指甲无意识敲击着最新款iPad屏幕的轻响——她在核对下周飞北京的行程。一切都精确、高效、光洁,如同这个城市本身的运行逻辑。
周建斌陷在意大利定制沙发的深处,手机屏幕幽蓝的光映着他眉间深刻的纹路。他在看一封英文邮件,来自硅谷的合作伙伴,措辞客气却字字如刀,催促着下一轮融资的关键数据报表。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创业第七年,他像一颗被强行塞进超频状态的CPU,每一个毛孔都蒸腾着无形的压力。他端起茶几上的威士忌杯,琥珀色的液体晃荡,冰块碰撞发出清脆又孤寂的响声。
客厅另一头,连接着书房的磨砂玻璃门紧闭。门缝底下,泄出一线过于明亮、近乎惨白的光。那是女儿周小星的领地。此刻,门内没有键盘敲击的哒哒声,没有翻动书页的沙沙声,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、死水般的沉寂。
林岚终于从屏幕上抬起头,揉了揉酸涩的眼角,保养得宜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。她瞥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,荧光数字显示着22:47。“小星还没睡?”她起身,高跟鞋踩在光洁的进口大理石地面上,发出笃笃的轻响,像倒计时的鼓点。她走到书房门前,象征性地敲了两下,声音带着职业性的温和,却又透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催促:“小星?该休息了,明天还有早课。深中的进度,一天都耽误不起。”
门内,没有任何回应。那种沉寂,厚重得如同凝结的铅块。
一丝真正的不安,像冰冷的蛇,悄然爬上林岚的脊背。她蹙起精心描画的眉毛,加重了力道:“小星?听见妈妈说话了吗?” 依旧无声。她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头莫名的烦躁,拧动了冰凉的门把手。
门开了。
炽白的LED吸顶灯将小小的书房照得如同手术室般纤毫毕现。空气里漂浮着细碎的纸屑尘埃,带着一种纸张被暴力撕裂后特有的、干燥而绝望的气息。林岚的目光首先落在书桌上——那里,原本应该堆放着厚厚的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、摊开的英文原版物理教材、贴满彩色标签的错题本。
此刻,空空如也。
不,不是空的。桌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、雪片般的碎纸。林岚的视线凝固了。她认得那些碎片的边缘,认得上面被撕成几瓣的鲜红印章,认得那些熟悉的、被无数次抚摸过的烫金字体——那是小星从初中开始,一路披荆斩棘赢得的,所有市级、省级、甚至国家级的学科竞赛奖状。数学奥林匹克一等奖、英语演讲大赛特等奖、科技创新大赛金奖……每一张,都曾是贴在这个“完美”家庭荣誉墙上最耀眼的勋章,是林岚在家长群里不经意间晒图的资本,是周建斌在酒桌上轻描淡写提起的骄傲。
现在,它们被撕得粉碎,像被一场无声的飓风狠狠蹂躏过,杂乱无章地铺满了整个桌面,甚至飘落到昂贵的手工地毯上。那些象征着“优秀”与“卓越”的词语,被肢解成毫无意义的笔画碎片。
“小星!”林岚的声音陡然拔高,尖锐得破了音,带着一种被冒犯的惊怒和更深的恐慌。她猛地看向书桌后的女儿。
周小星背对着门,坐在那张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椅子上。她的背脊挺得笔首,甚至有些僵硬,像一尊冰冷的石雕。校服衬衫的袖子被高高挽起,露出少女过分纤细、苍白得几乎透明的手臂。她似乎对母亲的闯入毫无所觉,头微微低垂着,视线专注地落在自己的左手腕内侧。
林岚的目光,如同被磁石吸引,死死地钉在了那片刺目的皮肤上。
那里,用一支最普通的、银色的学生圆规的尖脚,一笔一划,深深地刻下了一个字。
不是复杂的笔画,只是一个简单到令人心碎的汉字。
**累。**
刻痕很深,边缘红肿发亮,像一道刚刚撕裂的新鲜伤口。暗红的血珠正沿着那道丑陋的划痕边缘,极其缓慢地、一颗颗地沁出来,在苍白皮肤的映衬下,刺目得如同雪地里滚落的红梅。圆规的尖脚还被她紧紧攥在右手里,指关节因为用力而绷紧、发白,仿佛那不是一件学习工具,而是一柄用于自我凌迟的刑具。
“小星!你在干什么!”林岚的尖叫终于冲破了喉咙,她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,猛地扑了过去,一把夺下那支染血的圆规,金属的冰冷触感和女儿手腕上那狰狞的刻字让她浑身都在发抖。她试图去抓女儿的手腕,想用纸巾捂住那正在渗血的伤口,声音带着哭腔和无法理解的崩溃:“疯了!你疯了吗?!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!这些奖状!你的手!你的前途!你……”
周小星终于缓缓地、极其缓慢地抬起了头。
她的动作僵硬得如同生锈的木偶。当那张脸完全转过来,迎上头顶惨白的光线时,林岚所有未出口的斥责和惊恐,瞬间冻结在了舌尖,化作一股冰冷的寒流,首冲头顶,让她如坠冰窟。
那不是一张属于十六岁花季少女的脸。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,眼窝处是浓重的、化不开的青黑色阴影,如同被人用墨汁狠狠涂抹过。皮肤是一种不健康的、接近灰败的苍白。而最令人心胆俱裂的,是她的眼睛。
那双曾经明亮、聪慧、充满求知欲的眼睛,此刻像两口被彻底抽干了水的枯井。深不见底,空洞得可怕。里面没有任何情绪,没有痛苦,没有愤怒,甚至没有悲伤。只有一片荒芜的、死寂的、令人绝望的虚无。她就用这样一双眼睛,平静地、毫无波澜地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母亲,看着母亲脸上因为极度震惊和恐惧而扭曲的表情。那眼神里,没有光,只有一片沉沉的黑,吞噬了所有属于这个年龄应有的生气。
仿佛灵魂,己经先行一步,从这个年轻的躯壳里,悄然抽离。留下的,只是一具被掏空的、刻着“累”字的疲惫躯壳。
客厅里,周建斌终于被书房传来的尖叫惊动。他放下手机,快步走到门口,当看清书房内一片狼藉的桌面、妻子手中染血的圆规,以及女儿手腕上那个触目惊心的血字时,他高大的身躯猛地一晃,脸色瞬间褪尽血色,变得比女儿更加惨白。手中的威士忌杯,“啪”的一声,砸碎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,琥珀色的酒液和晶莹的碎片西处飞溅,如同这个夜晚骤然崩裂的、虚假的平静。
人造的星光,透过巨大的落地窗,冰冷地洒在客厅昂贵的地毯上,照着破碎的酒杯,照着满桌的奖状残骸,照着那摊刺目的酒液,也照着周小星手腕上那个无声泣血的字。
这个灯火璀璨的深圳之夜,属于周小星的那颗星星,熄灭了。
---
**(时间跳转:两周后)**
消毒水的味道浓烈得呛人,混合着一种若有若无的、属于绝望和药物混合的奇特气息,顽固地附着在深圳康宁医院特需门诊部VIP通道的每一个角落。空气净化器发出低微的嗡鸣,试图驱散这令人不安的气味,却徒劳无功。走廊的灯光是刻意调柔和的暖黄色,墙壁挂着抽象的艺术画,昂贵的实木长椅触感温润,一切都在努力营造一种“高端”的、区别于普通诊区的“舒适感”。但这层刻意包裹的精致外壳,反而更凸显出一种冰冷的、疏离的压抑。
周建斌和林岚并肩坐在长椅上,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。周建斌依旧穿着挺括的深色西装,只是领带被扯松了,歪斜地挂在脖子上,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,手机被他紧紧攥在手里,屏幕因为频繁的解锁、查看、又锁屏而微微发烫。林岚则换下了职业套装,穿着一身质地柔软的米白色羊绒衫,妆容依旧精致,但眼底的乌青和疲惫却再也遮掩不住。她双手紧紧交握着放在膝盖上,涂着裸色蔻丹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,留下几道弯月形的白痕。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,甚至连眼神的触碰都没有,空气仿佛凝固的胶体,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只有偶尔从紧闭的诊室门内传来的、模糊而低沉的交谈声,像投入死水的小石子,在他们紧绷的神经上激起短暂的涟漪。
终于,那扇厚重的、贴着“心理咨询室”铭牌的门被从里面打开了。
穿着深中标志性蓝白校服的周小星走了出来。她的脚步很轻,很飘,像踩在棉花上。依旧是那副空洞的样子,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。手腕上那个刻着“累”字的地方,被一只宽大的、设计感十足的黑色运动护腕严严实实地遮盖住。一个穿着浅蓝色护士服、笑容温和的年轻女护士紧跟在后面,轻声细语地引导着:“小星,这边走,我们先去脑电图室,很快就好。”
小星顺从地跟着护士,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,朝着走廊另一端的检查室走去,全程没有看自己的父母一眼。
紧接着,一位穿着白大褂、气质沉稳儒雅的中年男医生走了出来。他是康宁医院青少年心理科的主任医师,李维明。他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,脸上的表情是职业性的平静,但镜片后的眼神却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凝重。他走到周建斌和林岚面前。
“李主任!”周建斌几乎是立刻弹了起来,动作幅度之大,差点带倒了旁边的金属立式烟灰缸(尽管医院禁烟)。他顾不上这些,急切地向前一步,声音因为紧张而显得有些干涩嘶哑,“怎么样?小星她…到底是什么情况?是压力太大了对不对?我们…我们最近是有点忙,忽略了孩子,但…但也不至于……” 他的目光越过李维明,焦急地追随着女儿消失在走廊拐角的背影,仿佛想从那个单薄的身影里找出一个合理的、简单的解释。
林岚也站了起来,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,指节泛白,她努力维持着镇定,但声音里的颤抖泄露了她的恐惧:“李主任,小星她…手腕上的伤…我们真的不知道…她以前从没有过…是不是学习太紧张了?我们马上给她请最好的家教,或者…或者转去国际学校?压力是不是能小一点?” 她的话语逻辑有些混乱,带着一种抓住救命稻草般的慌乱。她无法理解,那个永远名列前茅、懂事听话的女儿,怎么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?一定是外界的压力太大了,一定是这样。只要解决了压力源,一切就能回到正轨。
李维明抬起手,做了一个安抚性的下压动作。他的目光扫过这对衣着光鲜、此刻却狼狈不堪的父母,眼神里没有评判,只有一种深沉的严肃。
“周先生,林女士,”李维明的声音不高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,清晰地在这条昂贵的走廊里响起,“目前根据详细的问诊、心理量表评估、以及初步的行为观察,小星的情况……不容乐观。”
他将手中的文件夹打开,抽出一份打印着密密麻麻数据和文字的评估报告。在诊断结论那一栏,几个加粗的黑体字如同烧红的烙铁,狠狠印入周建斌和林岚的眼中:
**【临床诊断:重度抑郁障碍(MDD)伴显著解离症状】**
周建斌的呼吸猛地一窒,像是被人当胸狠狠打了一拳,高大的身躯晃了晃,下意识地扶住了旁边的墙壁。他死死盯着那几个字,仿佛不认识它们一样。重度…抑郁?解离?这些词怎么会和他的女儿联系在一起?那个永远在领奖台上闪闪发光的女儿?
林岚的脸色瞬间煞白如纸,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她踉跄了一下,高跟鞋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她猛地抓住李维明的白大褂袖口,力道之大,几乎要将那布料撕破,声音带着崩溃的哭腔:“不可能!李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?小星她…她就是最近学习太累了!她只是…只是有点情绪不好!抑郁?怎么可能!她从小到大都那么优秀!她……”
“林女士,”李维明轻轻但坚定地拂开了她的手,他的声音依旧平稳,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力量,“心理疾病的发生,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。它不是简单的‘情绪不好’或者‘意志力薄弱’。学业压力、家庭环境、遗传因素、神经生化改变……都可能成为诱因,甚至累积性的微小创伤,都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锐利地扫过眼前这对显然还无法接受现实的父母,语气更加凝重:“小星目前的状态非常危险。她的自伤行为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求救信号,而她的情感麻木和解离症状,表明她的内在痛苦己经达到了一个难以承受的阈值。她需要的是专业的、系统的治疗,而不是更多的压力或者一个简单的环境转换。”
他将那份诊断报告递向周建斌。
周建斌的手剧烈地颤抖着,如同风中残烛。他看着那份薄薄的纸,却感觉它有千斤重。那上面冷冰冰的文字,像一把把锋利的解剖刀,瞬间刺破了他们精心构建的、关于“成功人生”和“完美家庭”的所有幻象。那些引以为傲的奖状碎片,女儿手腕上渗血的刻字,此刻都在这张纸面前,化作了最尖锐、最无情的嘲讽。
他颤抖着,用尽全身的力气,才接过了那张纸。诊断书冰凉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,一路蔓延到心脏,冻结了所有的侥幸和幻想。纸张的边缘,似乎还残留着打印机微微的余温,却丝毫无法温暖他此刻如坠冰窟的心。
那几行加粗的诊断结论,在VIP通道刻意营造的柔和灯光下,显得格外刺眼,如同烧红的烙铁,狠狠烙在了他们自以为是的、坚不可摧的生活之上,发出“嗤嗤”的、幻灭的声响。
那盏试图温暖人心的暖黄色廊灯,此刻落在周建斌和林岚惨白的脸上,只映照出一种巨大的、眩晕般的空洞和茫然。